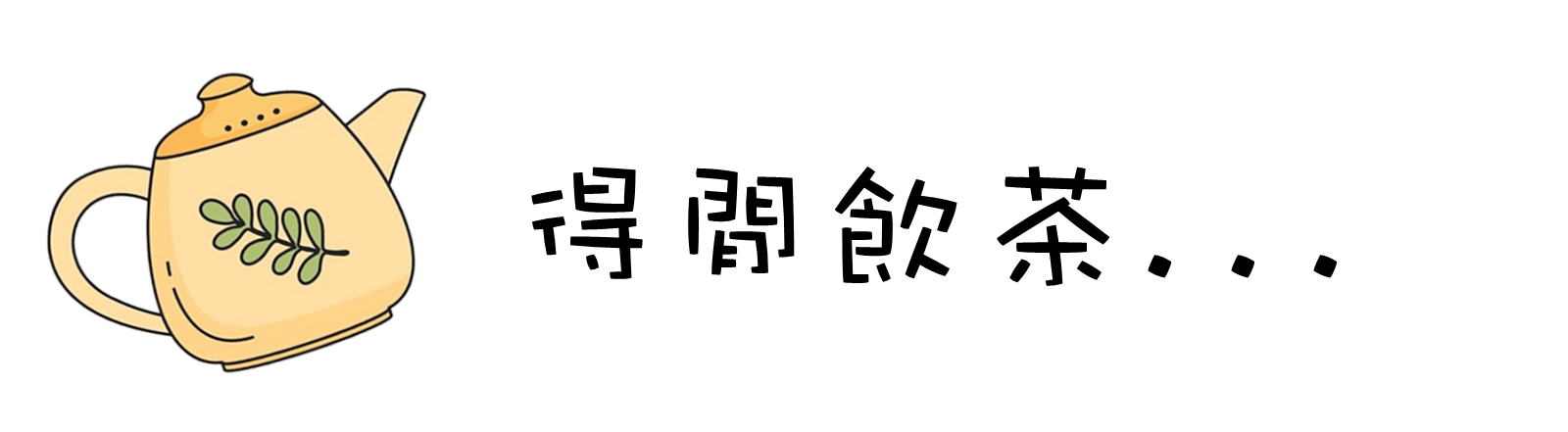晚上十一點半,我一邊打著哈欠,一邊還在「滑」著電腦上的臉書……身旁的手機此時嘟嘟地振動起來。我疑惑地扭頭看了看,螢幕上出現了一個微信添加好友的請求,但名字好像挺陌生的 — 「何麗麗」?!疑惑的剎那,我腦子裡也瞬間閃過好幾個模糊的人臉。我這個人別的不行,就記憶力這塊還是挺讓人震驚和佩服的。短短的一分鐘,我好像知道「她」是誰了。
何麗麗,對,她是我二十幾年前在內地上初中時的同窗。最近內地因為放寛疫情封控措施,再加上一些間接的原因,許多城市都有七八成的市民染上了新冠肺炎,而市面上一些退燒散熱的藥品也因此被搶購一空,市民們都在想辦法聯繫國內外的親朋好友幫忙購置這些應急藥物。這不,何麗麗不知通過甚麼渠道找到我,也是為了請我幫忙找尋及購買所需藥物。雖知這時本港市面上的退燒止咳藥物也正面臨缺貨的窘境,但為了不讓這位突然「到訪」的昔日同窗失望,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因夜漸深,不方便再打擾生病的朋友休息,我和她只簡單聊了幾句便草草收線。時鐘敲嚮十二點,本以為白天忙碌的工作能讓我一夜好眠,卻不知方才朋友的意外出現已擾亂了我的生理時鐘,我遲遲不能入睡,腦中的思緒漸漸把我帶到很遠很遠……初中?不,更遠……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出生在福建省某市某鎮的一個偏僻的小鄉村裡。這個鄉村雖說鄰里尚算和睦,談不上親近,村民的思想卻也因為環境的閉塞而顯得極為封建和保守。當時因為家裡面有移民港澳多年,過著富裕生活的親戚,這些親戚逢年過節就會給鄉下的家裡寄錢,或舉家返鄉探望老母親(我奶奶),帶著禮物金器,贈給親朋鄉鄰。而我爺爺也靠著拿這些錢給鄉裡修路而成為村裡人爭相膜拜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因著一家人當時無論走到哪裡都受人敬仰,身邊的小伙伴、甚至同學都似乎很羡慕嫉妒我。童年的我上的是鎮上的小學,周圍大多數同學都是來自附近的鄉村,家裡需要務農;只有一兩個背景跟我差不多,但家境卻比我要好上幾百倍的同學,後來我知道,打個比方,如果我家是百萬富翁,那麼那些同學的家就是億萬富翁之家。也是從那時起,我才開始明白原來人與人之間是有差距的,而這個差距是建基在視野的廣闊度和物質生活的豐富程度上的。因為在跟這一兩個「另類」聊天的時候,許多事情我聽不懂;而跟其他鄉下同學聊天的時候,許多東西我一樣聽不懂。想想,這也印證了時下流行的那句話叫「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
小學生活於我而言開心、平淡又無聊。讓我至今印深刻的除了人以外還是人。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我的成績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取得好成績於我來說並不太難,在與同學的相處上因著本身和善的性格倒也沒出過甚麼大問題。唯一令我感到頭痛和煩惱的是上六年級的時候,坐我後座上的那位男同學,那位看起來有點二楞子的傻大個,那位被老師叫上講台還在用髒手指摳鼻屎,並把鼻屎直接抹在講台上的傻大個。我痛恨他,我討厭他,光想到他我就覺得惡心。我記得那時六年級的每一節課,當我正專心聽課的時候,他的毛腳此時便會從課桌下延伸過來,並用那骯髒恐怖的腳趾,撩觸我裙下半截露出的大腿⋯⋯霎那間,我感到憤怒又羞恥,恐懼又惡心,可是我不敢出聲,我害怕一出聲,所有人都知道我發生了這樣的「糗」事,以後我還怎麼做人?於是在每一次我受到這樣的侮辱時,我只能用腳反向踢回去,那隻毛腳會反射性地縮回去,可是沒過幾分鐘就會再嘗試,而且屡試不爽,似乎「它」也知道原來我只有這般能耐。自此,穿裙子上課成了我的惡夢,卻又對人難以啟齒,耻辱與恐懼跟著埋在了我幼小的心靈裡。彼時,「性騷擾」這個詞還沒有被發明出來,童年已過,少女未滿的我在面對每一次的騷擾也因為害怕而選擇了沉默。
如今,在回想起小學這段可怕遭遇的時候,我已然沒有感覺,盡管我必須承認這個經歷在我心理上留下了一段長時間而可怕的陰影,也因此讓我永遠記住了那個傻大個。不知為何,對於小學生活的記憶我總是停留在那些晦暗的場景。除了記得自己被欺負,一些同班同學,會因為「身份卑微」,儼然也成為被欺侮的對象。是的,身份卑微再加上貧窮,本身在那個時代那個物質匱乏的地方就帶著原罪。就因為妳除了要幫家裡務農,平時還要忙著幫鄰居帶小孩,而鄰居給妳的回報只是一隻餡兒少得可憐的菜肉包子,妳一邊咬著包子,一邊對鄰居投去感激的微笑,手裡還抱著剛滿周歲哇哇啼哭的嬰孩,而這一幕剛好被路過的同班同學看在眼裡……那一天,有同學聲稱丟了耳環,並指證說是妳偷的,罵妳犯賤。於是妳被「請」上講台,在眾目睦睦之下被帶有嚴重偏見的老師賞了二十個大巴掌,被扇得火熱腫痛的臉頰,妳都不敢伸手捂。沒有眼淚,也沒有辨解,只有「震撼」和當下全場的鴉雀無聲……後來,終於有人承認是自己把耳環放錯了地方所以才找不到,耳環並沒有丟。可是,妳至始至終都沒有等來那句應有的道歉!
我在鄉下度過了開心又煩惱的小學六年,轉眼畢業後,媽媽把我的戶口遷到了附近的城市,自此我闊別了那令我又愛又恨的鄉村和小學同學,上了市區一所遠近聞名的重點中學,在那兒展開了我全新緊張又燒腦的中學生活。然而小學的過分安逸讓我產生了即使上了中學也不用太努力就可以拿高分的誤解,於是我一開始就處於極其鬆懈的狀態,直到初中一年級的尾聲,我的成績實際上已經是班上最後的那十名之一,那時一個班總共有五六十號人,而我的名次相當於在四十五至五十五之間徘徊。媽媽為此傷透了腦筋,從小就很愛面子的我也因為這樣的成績老感覺抬不起頭來。但即便這樣,已習慣懈怠的我努力的勁兒也維持不了一個星期,之後又是週而復始地鬆懈。那時,所謂的重點中學,有點像現在香港那些老牌名校,就好比聖保祿、拔萃之類的名校,入學的學生靠的是小學優異的成績和良好的操評,甚至還包括各種技能的打分。一考進這種名校,同學之間競爭會異常激烈,學生「壓力山大」,每個人都會為了能繼續在名校生存,為了能擠進班裡前二十名、年段前五十名而搏盡自己最後的一絲力量,所以學生的質素可想而知。也因此,學習成績差的人便成了整條無型鄙視鏈的末端,我不僅是班裡那個極不起眼的女生,同時還要承受那些聰明好學、成績永遠名列前茅的同學的歧視,這就是鄙視鏈的殘酷。也不是說學霸會對學渣做些甚麼,但是被故意忽視的感覺還是挺糟糕的。記得有一次物理測驗發了成績,當日的測驗是即測即改即評。有一道題好像是這樣的,一個桶置於盛滿水的水槽裡,桶沉到水槽底,問這個桶底部的浮力是多少。同學的答案五花八門,百花齊放,只有我答的是零,而這個答案是正確的。老師在台上說完答案,附加了一句,全班只有一個同學答對,霎時,班裡全都沸騰起來,同學都在猜測答對題的到底是「哪方神聖」。不知是出於學霸精準的預感,還是他的直覺,坐我前座的王明嵐,一枚妥妥的男學霸,回頭直接盯在我的試卷上看,「竟然是妳!」,他看完直視著我道。語氣中不僅沒有一點驚訝,還帶點輕蔑的嘲諷,似乎在說,「原來是你,也對,你這種不用腦子的傢伙才會直接答零!」……剛還在暗自竊喜的我一聽到這句語帶嘲諷的話,整個人一下子羞愧起來。是啊,原來是我,只有我這種頭腦簡單的人不用經過深思熟慮的演算就會立刻寫出這種答案。此刻,我從一個「自信滿滿」的成功者一下子墮落成無地自容的失敗者。
既然做了學渣,名次上不去,還要處處受人歧視,那我也認了,我就乖乖做我的學渣。還好我生來一副與世無爭的呆模樣,而且始終待人和善,很多同班同學還是挺喜歡我的,這其中就包括那位金德源同學,為何提起這個人?因為我猜測他可能因為我斷送了自己的前途。為何是猜測?因為在初中時代最後一次見到他之後,直到今天,我都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一個原因是在學時我壓根兒跟他就不熟,另一個就是這麼多年來這件事對我來說只是無足輕重的存在,只是一個微弱的記憶,而且我離開故鄉來到香港生活,故鄉的一切便已成為過去,我不想再追究過去的那些事,也許提起他,潜意識裡是想減輕我自身的愧疚感吧。那時,金同學坐我右邊的位置,我和他中間隔著一條走廊。他性格很開朗,形象卻有點像街邊的小混混,梳著八字頭,皮膚黝黑,學習成績也不算好,不過喜愛說笑,所以平時一到課間休息的時候,總能聽到他的說話聲和周圍同學的哈哈大笑。每當這時,一向沉悶自居的我也被他獨特的幽默搞得笑出聲來,而他看到我對著他笑,似乎有一點自豪,又帶著幾分不好意思。這樣的「日常」維持了一個學期之久,直到下學期的某段時間。我開始而且明顯發現金同學會有意無意地說笑,當說到笑點的時候,他會刻意向我投來「充滿曖昧」的目光。不光這樣,他甚至為了要更靠近我,吸引我對他的注意,時不時邊看我邊盡量傾斜身體向我這邊靠攏。也許是意圖太明顯,也許是我對戀愛還太陌生,我不僅以目光刻意迴避了他的曖昧,裝作看不見不知道,之後我也沒再「參與」他的笑話。而他以這樣的行為嘗試了差不多一個學期之後,也許是意識到我們之間的不可能,終於放棄了。而我那時並不知道我這樣刻意的忽視和迴避會給他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我只記得在看到他耷拉了兩天之後,突然毫無預警地從這個學校,這個城市人間蒸發了!一開始,我以為他只是自己跟自己賭氣不上學,直到之後過了一個星期,甚至一個學期,他都沒再出現過,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輟學了。為了不想再看到我,為了抗議我對他的刻意忽視。當然那時候天真的我怎麼也理解不了為何我的拒絶會成為「壓死」他的最後一根稻草。現在,到了這個年齡,我才明白拒絶一個人有很多種方式,可以明言,可以婉拒,偏偏就不能逃避或忽視,對有意與自己交往的人來說,用刻意的忽視去拒絕是最殘忍的!
「咇不咇不……」窗外路過的救護車聲終於把我從深思中拉回來。我借著月光看了看鐘,已是凌晨兩點多。嗯,明天還要上班,明天還有明天的煩惱,往日的一切也不過是煙雲,今日的我也不是昨日的那個我。我想每個人不論活到甚麼年紀,都須時刻督促自己反省與進步,我們都不是聖人,我們也會做錯事,但知錯能改總歸是好的。你說,對嗎?